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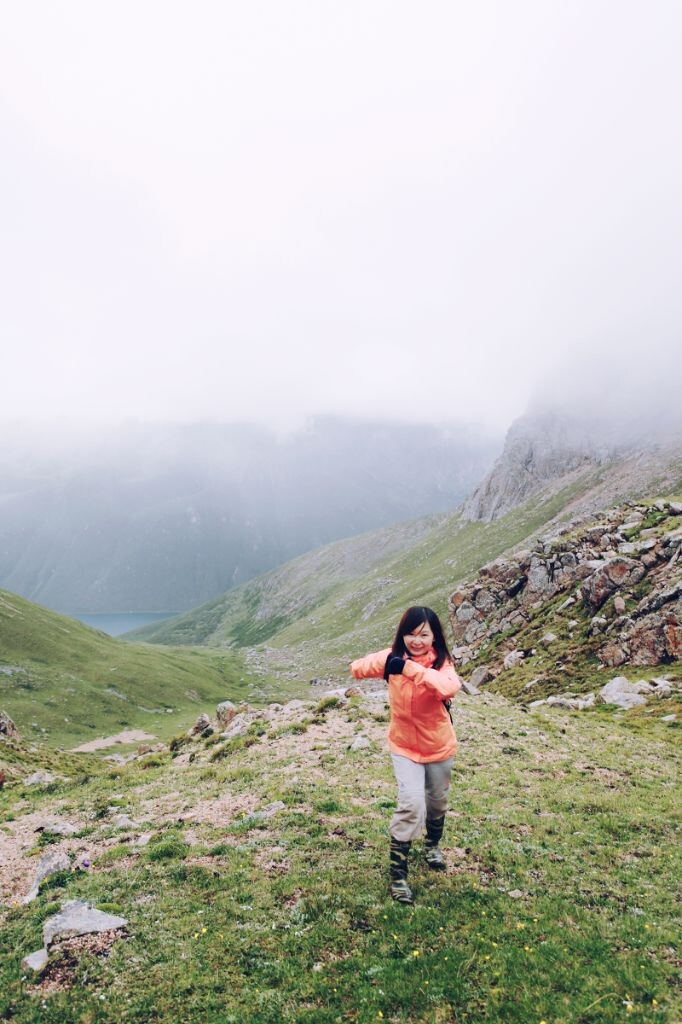
我也露个脸




婴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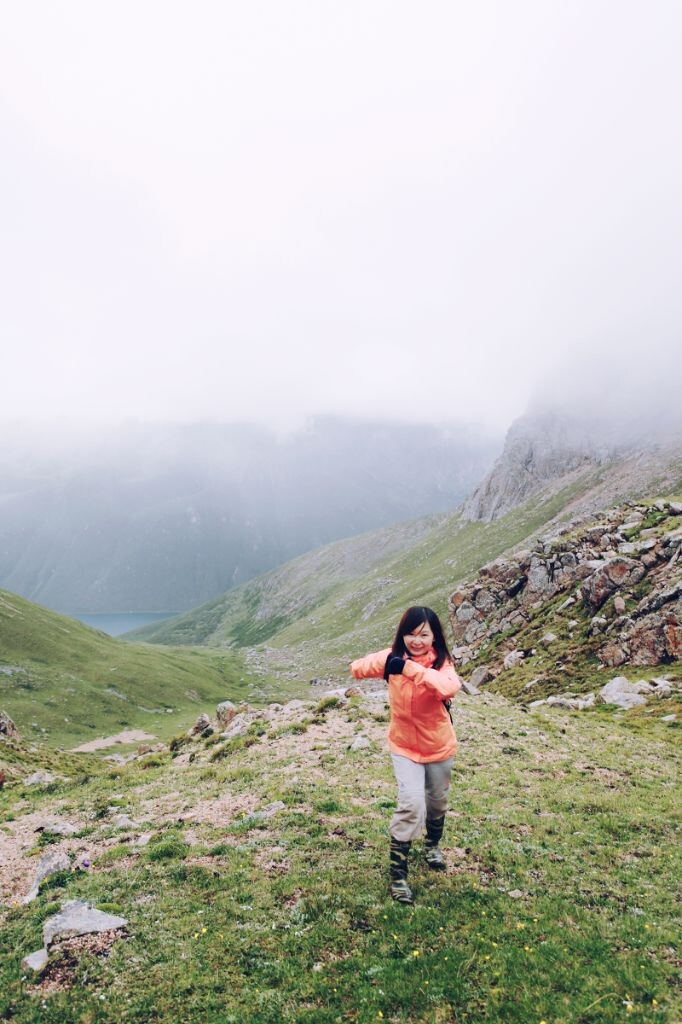
我也露个脸




婴



